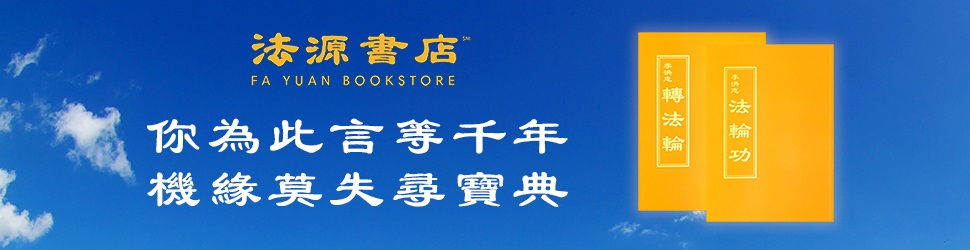|
|
 |
 |
 |
|
2023年7月22日
發表
人氣:56,738
分享:








|
|
|
| 文革初期林彪爲什麼想投奔蔣介石(圖) |
| |
|
顏昌海
|
【人民報消息】網上流傳着林彪在1966年11月給蔣介石一封密信,信中林彪表示了對他昔日校長蔣介石的感念和擁戴;也表明自己身處「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朝不保夕的處境。

| 文革初期毛澤東、林彪和劉少奇在天安門城樓上。(翻拍自萬維讀者網) |
文革初期林彪爲什麼想投奔蔣介石
林彪在中國,幾乎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但由於官媒的刻意掩蓋和歪曲,使人們看不到林的真面目。近年,由於林彪政治影響的淡化,一些關於林的檔案也被解密,林彪的真實形象也逐步顯現,甚至呼之欲出。近日,網上流傳着林彪在1966年11月給國民黨領導人的一封密信,當時正值「文革」爆發之初。信中的林彪表示了對他昔日校長蔣介石的感念和擁戴;也表明自己身處「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朝不保夕的處境。
這封信的可信度是比較大的。現在的人們基本清楚,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就是爲了搞掉政敵劉少奇,但毛澤東此時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也要拉攏掌握着軍權的林。表面上看上去,毛澤東與林關係密切,但林彪明白,毛澤東拉攏林,只是一時利用,說不定到時候也會卸磨殺驢。
從近年解密的《林彪日記》看,林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了然於心。林彪在1964年3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是福還是禍?毛囑:要我關注政局在變化,要我多參與領導工作,又問:上層也在學蘇聯,搞修正主義,怎麼辦?中國會不會出赫魯曉夫搞清算,搞了怎麼辦?毛澤東認爲被人架空,這個人是誰?我吃了一驚,冒了一身冷汗。一場大的政治鬥爭要來臨。林彪在1966年5月26日的日記更明確的寫道:老毛施陽謀外出,由劉主持中央會議,經劉除「彭、羅、陸、楊」作第一步,再通過毛的政治鬥爭綱領文件,剷除劉、周、鄧,這是毛的陰謀。
因此文革爆發後不久,林在給國民黨領導人一封密信中表示出對蔣介石的擁戴。
1966年11月,林彪、陶鑄密派黃埔四期同學蕭正儀赴香港同國民黨掛鉤,蕭正儀祕密會晤了旅港黃埔四期同學、曾任國軍華南補給區中將司令的周遊(按:此人在大陸易手時捲逃一筆鉅款潛往香港,以餘不足觀閣主筆名,在《春秋》等刊撰稿)。
密函內容如下:
「鐵兄:久未通信至念,回憶當年共硯黃埔,恍如隔世。兄天姿明敏,正應爲國家效力,乃退閒塾處,殊爲可惜,茲因文灼兄南行之便,特修寸楮致候,祈加指示。吾人處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朝榮夕,詭變莫測,因思校長愛護學生無微不至,苟有自拔之機,或不責已往之錯,肺腑之言準乞代陳爲感,此頌道安。
學弟尤鑄同啓十一月一日」。
林彪字尤肋,故信尾署名尤;鑄是當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副總理、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陶鑄。林陶二人早年均爲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生。1949年冬率國民黨18軍締造金門古甯頭大捷,後升任參謀總長與國防部長的高魁元是林彪同隊同學。高魁元身材魁梧站在排頭,林彪身材瘦小站在排尾。周遊字鐵梅,故林彪在這封密函中稱他爲鐵兄。雙方的表字只有彼此知道,雖然此信不是林彪親筆,但周遊認爲不可能是虛構的。信中「文灼兄」乃是蕭正儀的別號。
周遊穿針引線同國軍參謀本部特種軍事情報室駐香港特派員取得了聯繫,將此密函上呈特情室主任張式琦,張即向國防部長蔣經國請示。蔣表示要研究後再說,張式琦就決定同蕭正儀這條線保持聯繫。爲了取信於對方,張式琦將原函奉還,另由周遊署名覆函,交由蕭正儀帶回大陸面交林彪。蕭正儀返大陸前曾與周遊約定此後彼此聯絡的方式。蕭取道廣州,乘粵漢鐵路先到武漢,再到上海。他在上海曾函告周遊,稱尤、鑄二人未改初衷。但此後蕭正儀成了斷線風箏,同周遊失去了聯繫。
張式琦退休後定居美國洛杉磯。他歷任臺灣參謀本部特情室主任、國防部情報局局長達十二年,考績爲特優。臺灣軍情機關運用漁民蒐集大陸情報始自張式琦,在滇、緬、港澳以至美國各地建立情報基地都是他的顯赫業績。他回憶,國民黨回覆的核心內容有三點:「第一,我們向他表示他是受歡迎的。第二,我們願意幫助他保住他的特殊地位。且(最後),我們想逐漸發展這一關係。我們想盡最快的速度給林回信,因那時陶鑄被打倒了。」事實上,陶1967年1月倒臺,兩年後在醫院死於未經治療的癌症。就張式琦所知,從大陸來的消息停止了。但國民黨仍然相信他們在大陸政權最高層裏潛伏着一個盟友。
「在1966年到1971年間我們確信林姻定反對毛澤東」,張說,「那封信後,所有涉及到林彪的活動都被密切的關注。所有他的(激進)講話,所有他乾的事情都爲了一個目的──贏得毛澤東的信任。」
蕭正儀從上海寄信之後就消失了,周遊也於1968年死於香港。另一位確認此資訊交往這件祕聞的人是高龍,他是國防部情報局駐英國屬地香港的主要負責人,現居住在臺北。高說他幫助證實了原信並傳送了回信。「我們把此事看得十分重要」高龍說,這一祕密過程非常複雜,因爲「每一部分都緊緊相連。因爲保安措施嚴密,此事不可能輕易傳出去。」高說對於臺北回覆內容,他只知有限的一部分。但他認爲信中一定告訴林彪,國民黨會原諒他捲入共產黨的活動。高回憶那封信時說:「最重要的事是反對毛,並非反共。」
但是在1966年,林似乎與毛澤東正在度着蜜月一般。爲什麼他還要冒種種危險寫一封可能身敗名裂的信?一個可能的答案是因爲權傾一時的陶鑄被打倒,陶是中共在南方的負責人,也是林的盟友。這表明了在動盪的文化大革命中,沒有誰的地位是穩固的。早在1966年初毛澤東寫信給他的妻子江青,表達了他對林一篇關於政變的講話的不滿,毛澤東懷疑林的忠誠。雖然那封信直到很久以後才發表,中共官方承認此信曾由周恩來轉交給陶鑄去複印。如果是這樣,陶一定會提醒林。
紅衛兵制造的無情破壞以及遍及全國的混亂也許已震驚了林。作爲一個強烈的愛國者,他帶着使中國統一與強大的夢想參加革命,毛澤東的倒行逆施使他感到憤怒。林此時也許姻定取毛澤東而代之的時機到了。

文革初期林彪爲什麼想投奔蔣介石
臺灣中華宗教哲學研究社榮譽理事長、臺灣淡江大學李子弋教授說蔣介石畢生最大的遺憾是未能利用林彪──蔣總統對此曾向陶希聖多次提及。1993年10月在美國發行的中文報紙《世界日報》出現一篇有趣的文章,做蔣介石的私人醫生達40年之久的熊丸在文章中說:”我唯一一次見到蔣總統流淚是在他聽到林彪的死訊時。”李子弋說:「陶希聖告訴我(蔣)哭了,因爲他深感遺憾。那就是在1971年。這給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國民黨的老將無疑會對他們身經百戰的最高領袖爲一個人而哭泣感到不滿,更不要說是爲一個共產黨的元帥了。但是蔣可能是意識到他返回大陸的最後一點希望隨着林彪之死而消失了。
然而,林彪在「文革」初期爲什麼沒有投奔蔣中正?因爲當時局勢發生了變化,林彪也改變了主意。劉少奇、鄧小平倒臺後,林彪沒有被毛澤東即刻除掉,反而一躍而爲副統帥,成爲官場的第二號人物,也是毛澤東對林緊跟他的獎賞。對於這點,林彪在1969年3月21日的日記中寫道:「總理送來黨章草案定稿,把我列爲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總綱。我心不安,向總理提出:『是否不妥?誰提出的?主席意見呢?』總理告知:『是主席親自提議的,有指示。既然定了黨的副主席,當然是接主席的班,名正言順。』我還是建議徵求其他同志的意見。」
既然林彪成爲法定的接班人,那麼林就沒有必要投蔣,必竟投蔣的風險太大,坐飛機不知能不能飛出去,會不會被打下來,即使駕機飛往臺灣成功,得到什麼樣的待遇還是個未知數。林彪幫助毛澤東打下近二分之一的江山,將國民黨趕到小島臺灣,與國民黨官兵結下了深仇大怨,如果不能剷除毛澤東立下功勞,只是一家人投往臺灣,那蔣不一定接收他,即使蔣有接受林之意,他的下屬們也不一定能容納林和善待林。
此時林彪當上副統帥之後又有些受寵若驚,他改變初衷,迷迷糊糊地踏上了毛澤東安排的道路。林爲了保全自己討好毛澤東,他開始對毛澤東進行噁心的吹棒,爲毛澤東的「發燒」煽風點火、爲「文革」興風作浪。然而好景不好,沒有幾年,毛、林出現了分歧和矛盾,最終演變爲你死我活的鬥爭。在林彪「叛逃」前的一、兩年時間裏,林也是很清醒的,從「571工程紀要」來看,不僅是林彪,就是林26歲的兒子林立果也清楚的認識到毛澤東是個古往今來最大的暴君,要爲民除暴。從林立果的清醒認識看,他絕對受到父親林彪的影響,說明林對毛澤東的認識很清楚,即毛澤東多疑而又殘忍。但林最後還是敵不過毛澤東,最後據說是「逃往蘇聯」、「折戟沉沙」。
而蔣介石沙場論將,一直認爲林彪是黃埔生中的佼佼者,最厲害之處是「謀定而後動」,深得兵家之道,早年曾想收歸己有,卻神差鬼使放了這個人才。
提起黃埔,蔣介石就眉飛色舞,那是他一生事業之發祥地。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黃埔軍校共畢業23期學員,但他最器重的,還是前五期。在這五期學生中,他對第一期和第四期又最具感情,原因很簡單,第一期是他的開山大弟子,那時他一心撲在軍校的建設上,與學員朝夕相處,耳提面命,真是親如父子。用他自己的話說:「第一期學生可說由我親自指導出來的多,其中雖不能完全照預定計劃做到,但只在精神上說,差不多有十分之八,做到原來的希望了。」他報起黃埔一期生來,一個個都如數家珍,神色得意極了。至於二期生和三期生,因爲他們一入學就趕上了兩次東征,蔣介石戎馬倥傯,也沒有時間過多關心,所以那感情自然淡了點。到了第四期,因爲東征的勝利,廣東形勢又趨於穩定,他又能經常光顧黃埔島了,恰逢第四期選拔了不少優秀青年,讓人看了也開心。如後來大名鼎鼎的張靈甫、胡璉、高魁元、謝晉元,這些國民黨軍界的佼佼者,都是四期出來的,但蔣介石心中卻認爲,林彪才是最優秀的。
比如,在中山艦事變前夕,那一階段內部爭權奪勢鬥爭很激烈,讓他心裏煩躁,於是上黃埔島散散心,順便視察島上情況。恰巧,正逢四期步科的學生上戰術課,他也沒有驚動別人,悄悄地坐在了後面。課題以前不久發生的惠州攻堅戰爲例,說一說這次戰鬥的取勝要素。這一仗乃蔣介石親自指揮,他當然最熟悉不過了,於是聽得饒有興趣。
只見學生輪番上臺,口說筆劃,滔滔不絕,有人認爲此戰勝利乃在於步炮協作得力,有人認爲則是指揮果斷,士氣高漲,不一而足。蔣介石心裏哼了一聲,不置可否,惠州之戰,乃經典之作,以上所言,雖有幾分道理,但不是關鍵,想當年大戰之前,曾讓他費盡心機,絞盡了腦汁……。輪到林彪上臺了,只見他一臉怯生生的模樣,也不多言語,就開始在黑板上畫起惠州地形圖,他畫得很仔細,很投入,城郭民居,地勢地貌,山川河流,一一標點清楚。就憑這一手,蔣介石已不用往下看了,該生是個有心人,他把這一課給鑽研透了,熟悉得如同自己的掌紋。用兵之道,在於謀定而後動。林彪已經憑着其天生的稟賦接觸到了戰爭藝術的精髓。他悄悄地走出教室,吩咐隨行的人,下課後,讓林彪去校長室見他。
這一次談話,多年後蔣介石仍記住每一個細節,這林彪看似一個不諳世事的學生娃,卻是城府森嚴,惜語如金。在以往與人的談話中,蔣介石一向是多問少答,始終掌握着主動。但與林彪則難進行,對方從不多答一個字,每一句話都是經過深謀熟慮,卻是極得體,極中聽。蔣介石心中有一股怪怪的感覺,年輕人本應該血氣方剛,朝氣蓬勃,很少有像林彪這樣少年老成,這樣穩重,這樣有心機的。憑着直覺,他意識到坐在他面前的乃是難得一見之將才,但卻很難駕馭,讓人捉摸不透。
師生倆一問一答,這時校長辦公室祕書陳立夫推門而入,報告說,汪黨代表精衛也上黃埔島了,請蔣校長前往議事。「可惡。」蔣介石嘴裏罵了一句,自從廖仲愷死後,汪精衛接任了軍校黨代表職,又把手插到黃埔島來了,擠進蔣介石的勢力範圍,這讓他很惱火,也很無奈。汪精衛畢竟是廣東政府的一把手,他還得忍住氣與之虛與委蛇。
於是,他調轉身氣呼呼而去,卻忘了與林彪打聲招呼。
被孤零零甩在一旁的林彪感受到了一種巨大的污辱,作爲一名普通學員,他當然不知道國民黨高層的內幕,只以爲蔣介石那一聲「可惡」是衝着他來的。林彪一向心高氣傲,把這件事記下了,幾十年後都不能忘懷,有一次與自己的老部下黃永勝聊天,提及黃埔那段生活,林彪對蔣介石有如下評價:「蔣介石是個軍閥,他在黃埔時高高在上,對許多學員、教官都不尊重,很多人對他有反感。」
再說那天蔣介石撇下林彪走後,大概也感到了自己的失態,這是有損於他的形象的,因此也曾想過要彌補一二。但他太忙了,緊接着就是發動中山艦事件,向共產黨人大打出手,後來又忙於準備北伐戰爭,出發前,他才抽出時間又去了一趟黃埔島。
因剛發生過中山艦事件,黃埔島氣氛很凝重,蔣介石一整天都忙於訓話,又找了一些師生進行個別交流,林彪也是其中之一。幾個月不見,蔣介石發現,林彪更加沉默寡言,眼睛裏甚至閃過一絲戒備,他不知道林彪的底細,此人早在進入黃埔前就加入了共產黨,兩位兄長,林育南、林育英都是中共重要幹部,中山艦事件後,第一軍和黃埔軍校都在清理門戶,林彪的中共黨員身份是祕密的,所以未曾受到影響。但這還是讓林彪受驚不小,因此完全收拾起鋒芒,臥薪嚐膽,隱晦韜光,喜怒不形於色,渾身長滿了心眼,隨時準備應付各種各樣的問題。蔣介石向林彪許諾,畢業後讓他來總司令部工作。
這個許諾太誘人了,當時蔣介石已取代汪精衛成爲廣東政府第一號人物,乃北伐軍主帥,當時黃埔畢業生都以能進入第一軍爲榮,那是天子門生,地位特殊。更不用說在蔣介石身邊工作,更是天子近臣了,非黃埔生中最優秀、最受蔣氏青睞者不敢奢想。
如果不是共產黨員的身份,林彪也許會感激涕零,但他是組織裏的人,有着組織裏的安排,組織裏的紀律。他知道上級對他畢業後的去處已經有了意向,將他分配至葉挺的獨立團,那是中共所掌握的第一支正規武裝。所以,他只淡淡地回答了一句:
「感謝校長的信任和栽培。」
見林彪並不領情,蔣介石感到了失望,怏怏道:「好吧,我出征在即,今後再和你聯繫。」
誰知這一別,師生兩人竟成陌路,從此分爲兩個營壘,成了敵人,成了對手。 △
(轉自萬維讀者網)
|
| 文章網址: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23/7/22/76869b.html |
|
 打印機版 打印機版
|
|
|
|
|
|
 |
 |
 |
|


本報記者
專欄作者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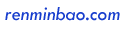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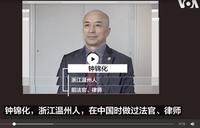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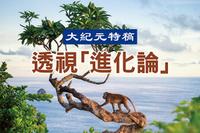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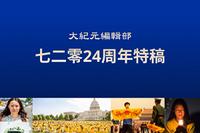








 打印機版
打印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