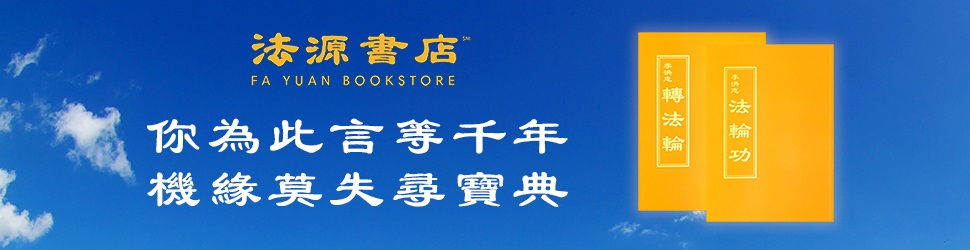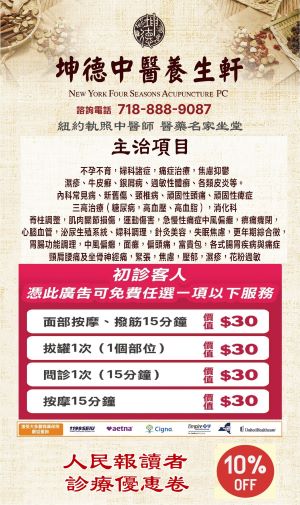習近平正定朋友賈大山。
習近平正定朋友賈大山。【人民報消息】農曆癸巳年末(2013年),河北作家康志剛在其博客上貼發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於1998年發表的一篇悼念文章《憶大山》,記述了一段塵封的往事,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文章經《光明日報》等多家報刊轉載後,引起國人強烈關注。臘月二十三(小年,2014年1月23日),我趕到正定,拜訪了幾位當事人。舊事重溫,感慨良多…… 1982年3月,習近平到正定縣任職後,登門拜訪的第一個人就是賈大山。 但是,兩人的初次見面並不順利。 關於這次見面的地點和人員,坊間流傳多種說法:有說是在大山家裏,有說是在其辦公室,有說他正在與衆文友聊天,還有文章明言在座者只是李滿天。 採訪中,筆者曾多方考證,得到的事實是:當天晚飯後,習近平請李滿天陪同,一起去尋訪大山。先是去家裏,不遇,後又趕往其供職的縣文化館。 李滿天不是他人,正是歌劇《白毛女》故事的第一位記錄整理者,時任中國作協河北分會主席,在正定縣體驗生活,是大山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彼時,大山正在辦公室裏與幾個文友討論作品。他當過老師、編劇、導演和演員,博聞強記,口才極佳。那是一個文學的年代,到處是文學青年,到處是文學論壇。他的屋內,更是常常訪客盈門。 李滿天是常客了,不必客套,而習近平穿着一件褪色的綠軍裝,雖然態度謙恭,滿臉微笑,但畢竟年輕啊,像一名普通的退伍兵,又像一個青澀的文學青年。或許正是因此,當兩人進來的時候,談興正濃的大山就沒有停止他的演說。 近平悄悄地坐下來,靜心地聽,耐心地等。 等了一會兒,趁大山喝水的間歇,李滿天上前介紹。大山這才明白,面前這位高高大大、清清瘦瘦的青年,就是新來的縣委副書記。 接下來,賈大山的反應讓習近平印象深刻。2009年7月號出版的期刊《散文百家》,整理發表了習近平2005年回正定考察時的錄音:「我記得剛見到賈大山同志,大山同志扭頭一轉就說:『來了個嘴上沒毛的管我們!』」儘管這話是大山對着滿天壓低聲音說的。 我們實在無法臆想當時的場景,抑或大山的語氣和表情。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時的賈大山還不到40歲,已獲得全國大獎,作品收入中學課本,聲名正隆,風頭日盛,加之天生淡泊清高的性格,面對這個比自己年輕十多歲的陌生的縣領導,有一些自負是可以想象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習近平並沒有介意,依然笑容滿面。 現場的空氣似乎停滯了一下。但不一會兒,氣氛就重新活躍起來。主人和客人,已經握手言歡了。 習近平在《憶大山》一文中記錄了當時的情景:「雖然第一次見面,但我們卻像多年不見的朋友,有說不完的話題,表不盡的情誼。臨別時……我勸他留步,他像沒聽見似的。就這樣邊走邊說,竟一直把我送到機關門口。」 那是一個早春的晚上,空氣中飄浮着寒意,也一定瀰漫着芳香。因爲,所有的花蕾,已經含苞待放了…… 正定古稱常山、真定,春秋時期爲鮮虞國。秦立三十六郡,常山有其一。自漢至宋元,真定始終居於冀中南龍首之位,與北京、保定並稱「北方三雄鎮」。明清至民初,包括石家莊在內的周圍14個州縣,皆屬正定府轄區。 正定城牆周長24裏,設四座城門。每座城門均用青條石鋪基、大城磚拱券,並設裏城、甕城和月城三道城垣。這種格局十分鮮見,足以說明正定作爲京南屏障的特殊地位。高大的城圈內,有九樓四塔八大寺,更有着衆多的商鋪、戲院、酒肆和茶樓。「花花正定府,錦繡洛陽城」,此之謂也。 古城正定,敦厚、傳統且深邃,像一株繁茂的大槐樹,綻放着細密的葉芽和花穗,散發着濃郁的清香和氧氣。 賈大山1942年7月生於古城西南街,祖上經營一家食品雜貨店鋪,家境小富。說起來,他的出世頗具傳奇。父母連着生產八個姑娘,直到第九胎,才誕下這個男丁。他從小備受寵愛,吃、穿、玩、樂悉聽尊便。他喜歡京劇,愛唱老生,還能翻跟頭,拿大頂。他更愛好文學,中學期間便開始發表作品。 高中畢業後,因爲出身歷史等原因,大山未能走進大學。他先是去石灰窯充當壯工,後又被下放農村。 正是這種特殊的人生際遇,他熟悉了市井文化和農村文化。這兩種文化交融發酵,蒸騰昇華,促使他成爲一名作家。1977年,他發表短篇小說《取經》,震動文壇,並在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中折桂,成爲河北省在「文革」之後摘取中國文學最高獎的第一人。無限風光,一時無兩。 大山身材中等,體魄壯實。關於他的面貌,他的朋友鐵凝曾經有過一段精準的描述:「面若重棗,嘴闊眉黑,留着整齊的寸頭。一雙洞察世事的眼:狹長的,明亮的,似是一種有重量的光在裏面流動,這便是人們經常形容的那種『犀利』吧。」 賈大山,的確是一位奇才。 他的創作習慣也迥異常人:打腹稿。構思受孕後,便開始苦思冥想,一枝一葉,一櫱一苞,苞滿生萼,萼中有蕊,日益豐盈。初步成熟後,他便邀集知己好友,集思廣益。衆人坐定,只見他微閉雙目,啓動雙脣,從開篇第一句話,到末尾最後一字,包括標點符號,全部背誦出來,恰似京劇的唸白。他的記憶,猶如一個清晰的電腦屏幕。朋友提出意見後,他仍在腹內修改。幾天後,再次詠誦。 三番五次之後,落筆上紙,字字珠璣,一詞不易,即可面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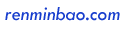



























































 打印機版
打印機版